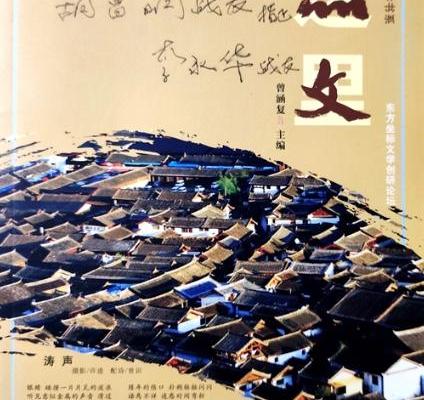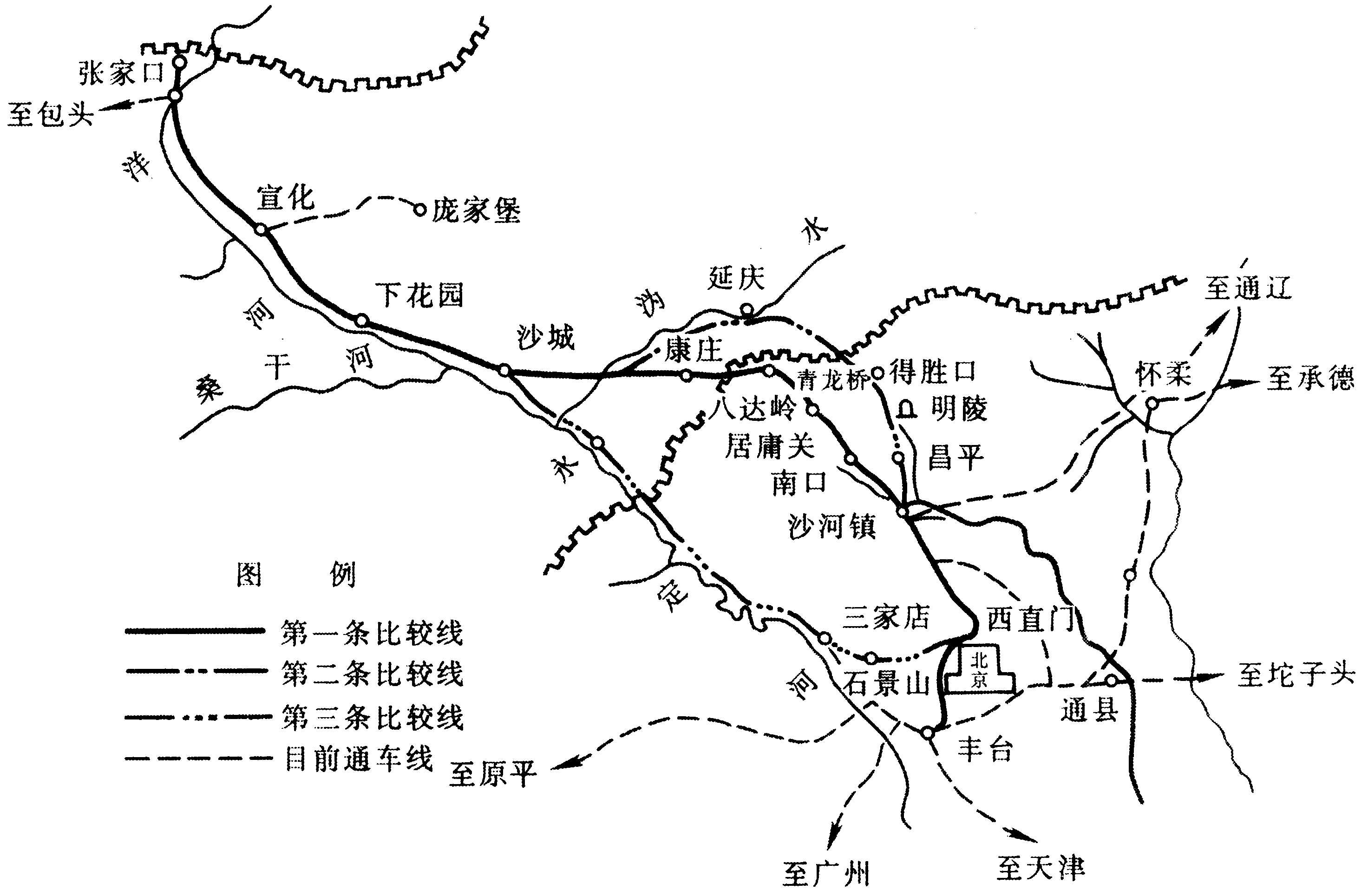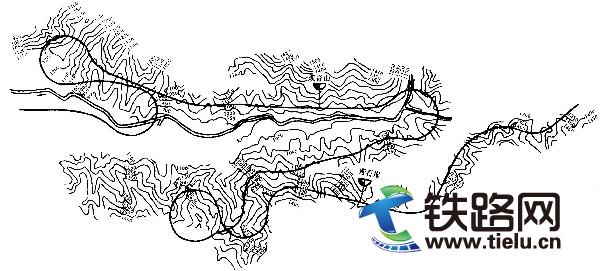晨光穿透苗嶺的薄霧時,我總愛數著鋼軌上的鉚釘散步。這些銀亮的凸起像年輪般記錄著四十三年光陰——從青澀的養路工到兩鬢斑白的中層干部,鐵軌始終以它恒定的間距,丈量著我生命的寬度。
塵世浮沉中,我漸漸懂得生活的悖論:肩上扛著道砟般沉重的責任,靈魂卻要保持著鋼軌般的筆直。年輕時總困惑于"燈下黑"的無奈,那些深夜搶修后獨自啃冷饅頭的時刻,也曾懷疑過堅守的意義。直到那個黎明,看見第一班列車安全駛過自己檢修的彎道,車窗里閃過旅客安睡的側臉,突然明白:負重前行的意義,就在于讓他人的旅途能夠輕盈。
我見過太多人生百態。有旅客為丟失車票暴跳如雷,也有姑娘把結婚喜糖塞滿我的工具包。這些記憶像鋼軌接縫處的伸縮縫,教會我在剛硬中保留柔軟的余地。真正的涵養,是像道岔轉換器那樣,既有精確的原則性,又有圓融的變通力。那些經得起時光打磨的人,都懂得在規章與溫情之間找到平衡點。
苗嶺的杜鵑開了又謝,我始終保持著工務人的習慣:俯身聆聽鋼軌的震顫。這聲音里藏著生活的隱喻——遠方傳來的轟鳴是夢想,枕木間的蟲鳴是日常。幸福從來不在遙遠的站臺,而在當下鐵搗鎬與道釘碰撞的清脆回響里。當年輕人問我如何忍受單調的重復,我就指給他們看鋼軌:看似千篇一律的延伸,實則每公里都承受著不同的應力與磨耗。
如今我的腦海里,鋼軌人生與燃情歲月并肩而立。時代在變,但有些東西永遠不變:道釘必須垂直敲入,就像做人要堂堂正正;曲線地段要加密枕木,如同人生低谷激情融化大雪覆蓋的線路。這些故事不是沉甸甸的勛章,而是像信號燈般,給后來者照個亮。
站臺上,我看著動車組如銀箭般掠過傳統綠皮車的窗口。四十三年的光陰在鋼軌上流淌成河,而我只是河床上一粒道砟。但每當列車駛過時那有節奏的鏗鏘聲響起,我就知道:這條鐵軌的歌聲里,永遠有我們工務人譜寫的音符。
免責聲明:本網站所刊載信息,不代表本站觀點。所轉載內容之原創性、真實性、完整性、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,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自行核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