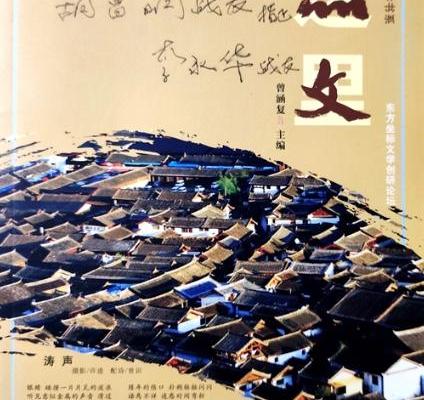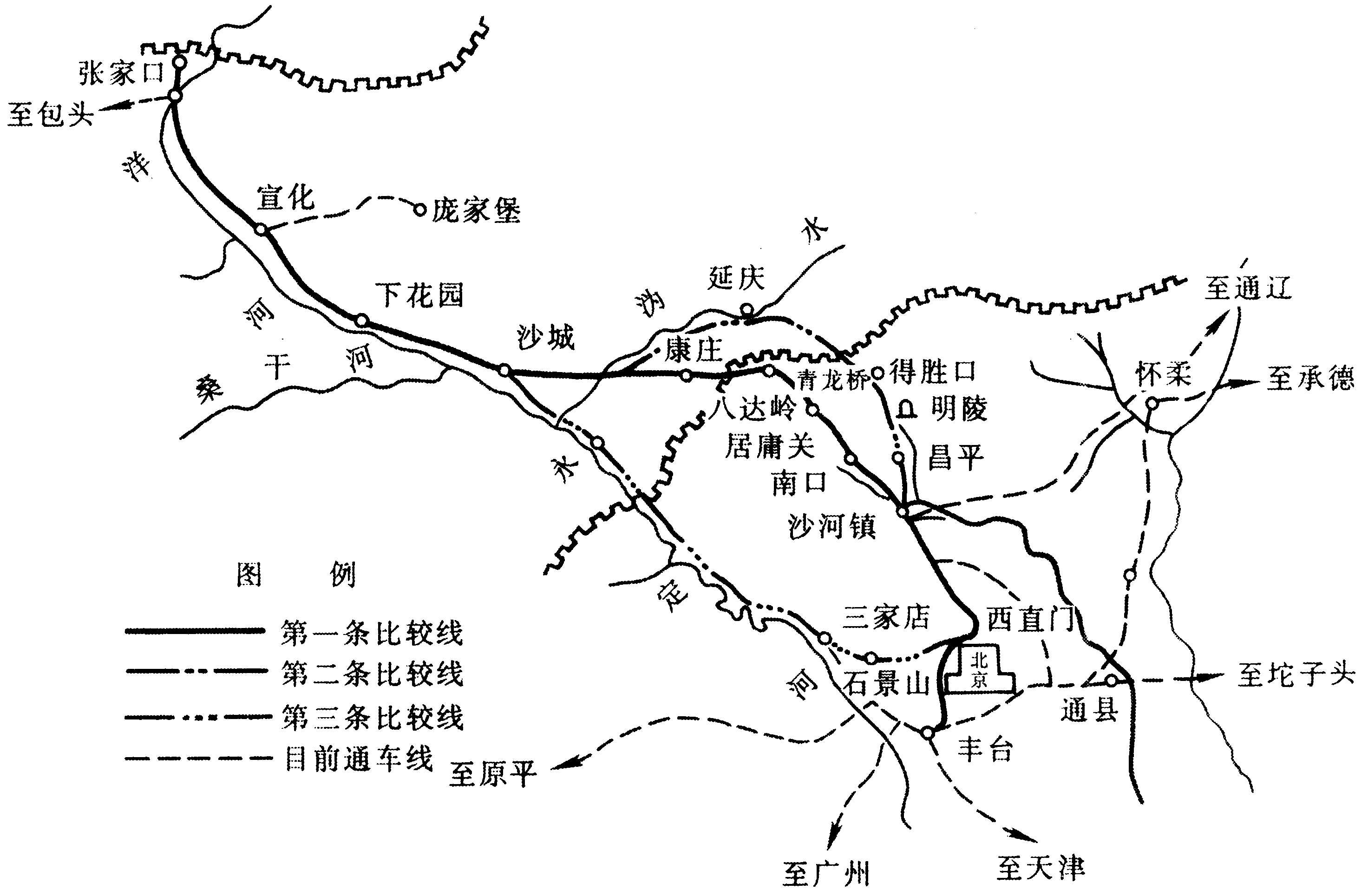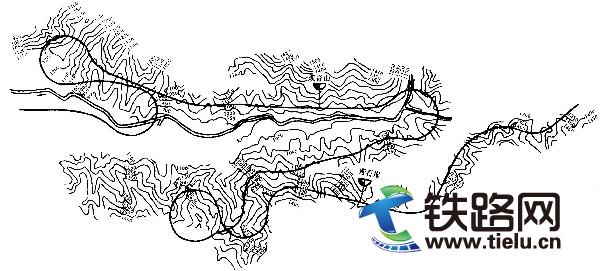暮色四合,群山靜默,唯有那皎潔的月光,如同最細(xì)膩的銀粉,溫柔地灑在綿延不絕的枕木上,為它們鍍上了一層朦朧而圣潔的銀輝。我,一個(gè)在這條鐵路線上奔波了四十余載的老鐵路人,此刻正踏著這些間距均勻、如同巨大鋼琴琴鍵般的軌枕,一步一步,沉穩(wěn)地走向大山的腹地。腳下的每一塊枕木,都承載著歲月的磨礪與火車的重壓,它們沉默不語(yǔ),卻向我傳遞著熟悉的溫度與力量。
這條蜿蜒曲折的鐵路,在夜色與山影的勾勒下,活像一條從遠(yuǎn)古沉睡中蘇醒的巨龍,它的身軀矯健而堅(jiān)韌,盤踞在層巒疊嶂的崇山峻嶺之間。它時(shí)而昂首穿過(guò)深邃的隧道,時(shí)而俯身越過(guò)凌空的橋梁,日夜不停地吞吐著南來(lái)北往的列車,將旅客的期盼與貨物的重量,穩(wěn)穩(wěn)地送達(dá)遠(yuǎn)方。每當(dāng)我的雙腳踏上那泛著冷光、不斷向遠(yuǎn)方延伸的鋼軌,心底便會(huì)涌起一股難以言喻的踏實(shí)感。這并非憑空而來(lái)的情緒,而是幾十年如一日,與鋼軌、枕木、道砟為伴,在風(fēng)霜雨雪中巡查、養(yǎng)護(hù)、檢修所養(yǎng)成的職業(yè)本能,更是一種早已融入血脈、刻進(jìn)骨子里的生命印記——我屬于這里,屬于這條鋼鐵巨龍。
清晨或傍晚,山風(fēng)總會(huì)如期而至,掠過(guò)成片的松林,掀起陣陣雄渾的松濤,那聲音仿佛遠(yuǎn)古的呼喚。山澗的清泉,不舍晝夜地流淌,叮咚作響,叩擊著溪底圓潤(rùn)的卵石,譜寫出自然的樂(lè)章。在這橋隧相連、綿延不斷的鐵路線上,一列列火車呼嘯而過(guò),它們的身影劃破晨曦,又融入暮色,仿佛一位技藝精湛的裁縫,將散落的晨光與暮色巧妙地縫合成一幅連貫而流動(dòng)的生活畫(huà)卷。極目遠(yuǎn)眺,遠(yuǎn)處山脈的剪影在天際線上起伏,宛如畫(huà)家筆下尚未干透的水墨丹青,帶著幾分寫意與蒼茫。天光,那最純凈的亮色,從峰巒的褶皺里悄然滲出,為天邊的云層鑲上一道璀璨的金邊,壯麗而肅穆。而在這幅宏大而流動(dòng)的山水長(zhǎng)卷之中,我們那個(gè)不起眼的小站,就像一枚安靜的鈐印,默默地蓋在這片土地上,見(jiàn)證著南來(lái)北往的匆匆步履,守護(hù)著每一次平安的抵達(dá)與出發(fā)。
工區(qū)的夜雨,總帶著一種別樣的韻味,不似城市的喧囂,卻有山野的清新。當(dāng)夜幕降臨,雨滴便開(kāi)始不緊不慢地敲打在宿舍的彩鋼瓦屋頂上,那“嗒嗒嗒”的節(jié)奏,清脆而富有韻律,恰似兒時(shí)母親在床邊哼唱的搖籃曲,單調(diào)卻充滿了撫慰人心的力量,讓奔波了一天的我們,在這自然的催眠曲中安然入夢(mèng)。余光中先生曾說(shuō):“雨不但可嗅,可觀,更可以聽(tīng)……”此刻,這詩(shī)句突然有了最具象、最生動(dòng)的注腳。然而,小站人的故事,遠(yuǎn)比這纏綿的雨聲更令人輾轉(zhuǎn)反側(cè),更值得細(xì)細(xì)品味。那些在工余飯后,沾滿了機(jī)油味的爽朗笑談,那些藏在一本本泛黃的施工日志里,日復(fù)一日、年復(fù)一年的默默堅(jiān)守,那些在艱苦環(huán)境中閃耀的人性光輝,都化作了我筆下源源不斷的靈感,讓我的鋼筆在稿紙上不知疲倦地耕作了整個(gè)通宵,試圖將這些平凡而偉大的瞬間永遠(yuǎn)定格。
花甲之年,歲月的風(fēng)霜在我臉上刻下了痕跡,也讓我的心境愈發(fā)沉淀。我愈發(fā)懂得,夢(mèng)想的真諦,并非一定要是腰纏萬(wàn)貫的金山銀山,也并非一定要是萬(wàn)人敬仰的顯赫聲名。它可以平凡,可以樸素,卻必須滾燙而真誠(chéng)。當(dāng)我在熱火朝天的集中修現(xiàn)場(chǎng),親眼目睹那鋼鐵巨無(wú)霸般的大機(jī)搗固車,精準(zhǔn)而高效地吞吐著長(zhǎng)達(dá)96公里的軌排,將每一寸鋼軌都搗固得堅(jiān)實(shí)平穩(wěn);當(dāng)我看到打磨車伸出它靈活的“手臂”,在漆黑的鋼軌上辛勤作業(yè),飛濺的火花如同節(jié)日的禮花,點(diǎn)亮了長(zhǎng)達(dá)2公里的線路;當(dāng)我看到身邊的工友們,用那雙布滿老繭、青筋突起的手,一絲不茍地調(diào)整著第13組曲線的超高,確保列車通過(guò)時(shí)的絕對(duì)平穩(wěn)……在這一刻,我找到了比任何華麗辭藻都更加動(dòng)人、更加有力的表達(dá)。他們那因長(zhǎng)期熬夜而深陷的眼窩,那在寒冬臘月里結(jié)滿白霜的眉梢,那被汗水浸透又風(fēng)干的工裝,都是鐫刻在鋼軌上的最美詩(shī)行,質(zhì)樸無(wú)華,卻字字千鈞。
記得那是十二月二十七日,一個(gè)天寒地凍的清晨,當(dāng)?shù)谝豢|晨曦艱難地穿透厚重的晨霧,最后一組道岔的打磨作業(yè)終于順利完畢。看著工友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,從彌漫的晨霧中緩緩歸來(lái),他們的臉上寫滿了倦意,身上落滿了塵土與霜花,我的鼻子突然一陣發(fā)酸,一股熱流涌上眼眶。為了按時(shí)完成這次緊急的集中修任務(wù),他們背著近三十斤重的檢修機(jī)具,在崎嶇的山路與冰冷的鋼軌間跋涉了整整二十個(gè)晝夜,風(fēng)餐露宿,攻堅(jiān)克難。然而,即便是在如此疲憊的狀態(tài)下,他們路過(guò)山腳下的村莊時(shí),仍記得幫助焦急的老鄉(xiāng)找回了跑丟的羊羔,那淳樸的笑容和略帶沙啞的安慰,溫暖了整個(gè)寒冬。這種刻在骨子里的溫柔與善良,或許就是我們山區(qū)鐵路人最彌足珍貴的品質(zhì)——既有鋼軌般的剛毅、堅(jiān)韌與擔(dān)當(dāng),守護(hù)著線路的安全暢通;又有道砟般的柔軟、質(zhì)樸與奉獻(xiàn),溫暖著身邊的每一個(gè)人。
如今,每當(dāng)我站在站臺(tái)上,聽(tīng)見(jiàn)遠(yuǎn)方傳來(lái)車輪與鋼軌那富有節(jié)奏的“哐當(dāng)、哐當(dāng)”聲,那聲音不再是單調(diào)的噪音,而是一曲深情的唱和,是鐵路人用生命譜寫的樂(lè)章。我總會(huì)想起退休老工長(zhǎng)臨別時(shí)對(duì)我說(shuō)的那句話,他的眼神堅(jiān)定而深邃:“小子,記住,咱們養(yǎng)護(hù)的不是冷冰冰的鐵疙瘩,那是千萬(wàn)人回家的路,是無(wú)數(shù)家庭的期盼與團(tuán)圓。”是啊,這條用我們的青春、汗水乃至熱血丈量的鐵道線,早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而我的鋼筆,這支曾試圖描繪山河壯麗的筆,終于也找到了它真正的“道釘”與“軌枕”——那就是用最真摯的情感,記錄下這些平凡英雄的堅(jiān)守與奉獻(xiàn),讓他們的故事,如同這延伸的鋼軌一般,永遠(yuǎn)流傳下去。
免責(zé)聲明:本網(wǎng)站所刊載信息,不代表本站觀點(diǎn)。所轉(zhuǎn)載內(nèi)容之原創(chuàng)性、真實(shí)性、完整性、及時(shí)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,請(qǐng)讀者僅作參考并自行核實(shí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