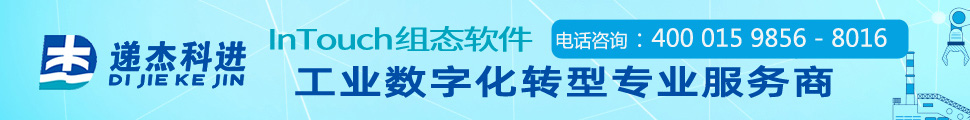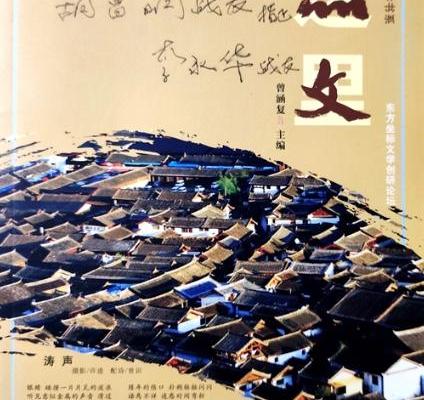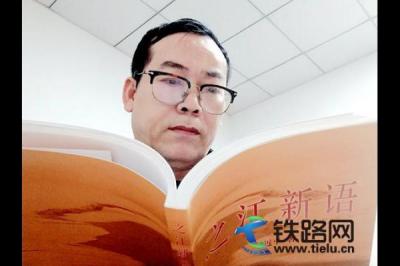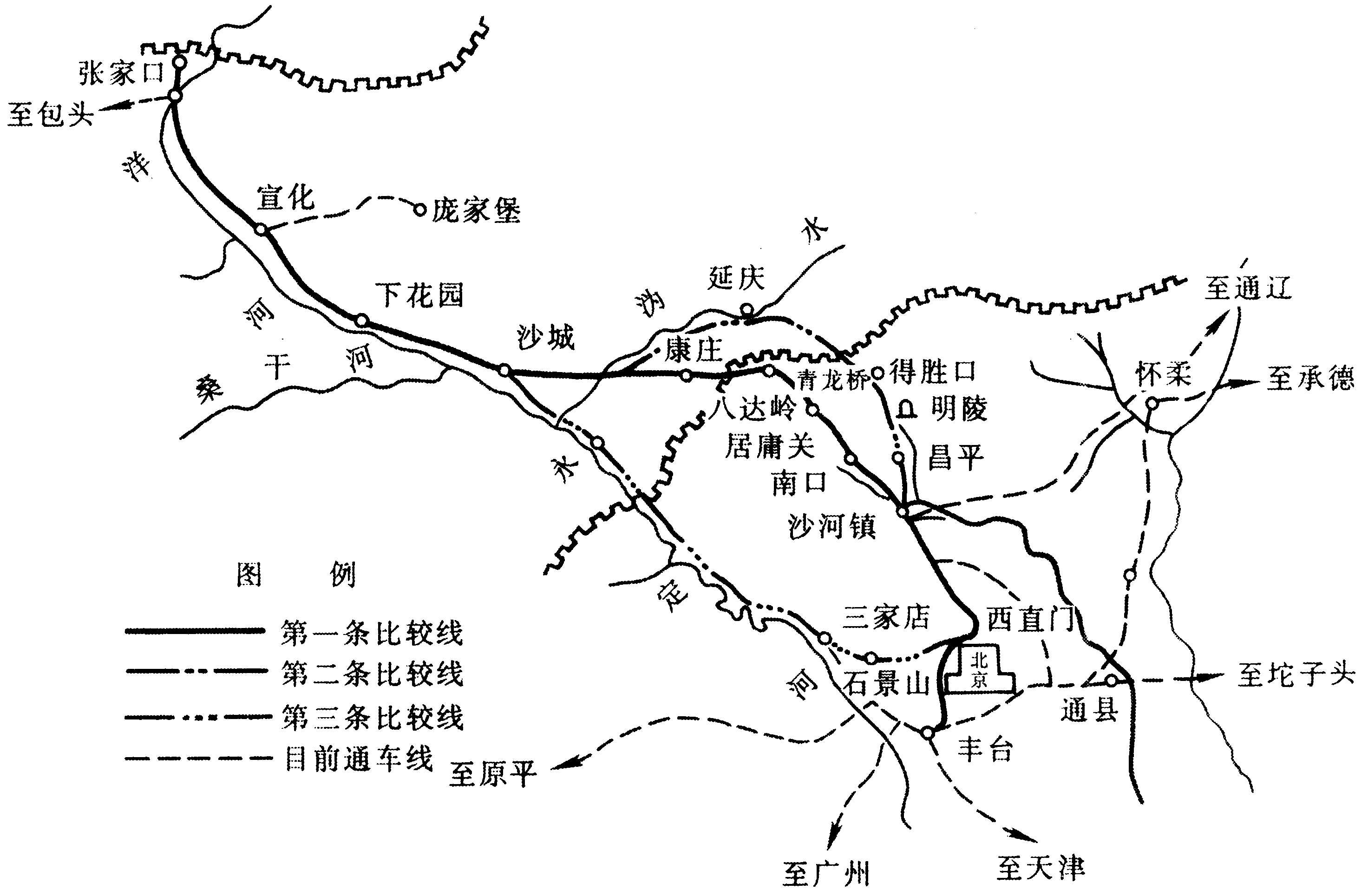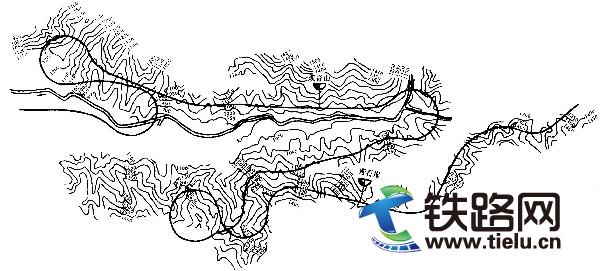晨光中的信號(hào)燈還懸著夜露,小站的鐵軌已開(kāi)始吞吐朝陽(yáng)。四十三年鋼軌人生,恰似那列永不停歇的綠皮火車,在苗嶺侗鄉(xiāng)的褶皺里畫(huà)出銀色的年輪。每當(dāng)車輪碾過(guò)接軌處的縫隙,便有一串顫音落進(jìn)山谷,那是時(shí)光在鋼軌上刻下的密紋唱片。
我珍藏著一張1985年的換軌作業(yè)單,泛黃的紙頁(yè)上油漬與指紋重疊,記錄著初踏鐵路時(shí)笨拙的青春。那時(shí)不懂兩根平行鋼軌的哲學(xué),只道是兩條冰冷的直線。如今才明白,正是這永恒的平行,讓千萬(wàn)次擦肩而過(guò)的列車,都能守住自己的軌道。
在那個(gè)扎根小站的煤油燈下,老工長(zhǎng)的記事本正在書(shū)寫(xiě)第三十九個(gè)春節(jié)。泛黃的紙頁(yè)間夾著女兒出嫁時(shí)的車票,那是他唯一缺席的重要時(shí)刻。“除夕夜在工區(qū)留守”,這行簡(jiǎn)短的記錄背后,是三十八碗沒(méi)吃完的餃子。
工長(zhǎng)室里,女職工小李正在霜花密布的玻璃上哈氣作畫(huà)。她凍紅的手指在鍵盤(pán)上起舞,編織出的不僅是列車時(shí)刻表,更是大山深處精準(zhǔn)的脈搏。那些被手套磨破的毛線,最終都變成了鋼軌上的紅色嫁衣。
巡道工老楊的背影是移動(dòng)的里程碑。他腰間別著的道釘錘,曾在暴雪夜敲醒結(jié)冰的道岔。月光為他鍍上銀邊時(shí),工裝后背析出的鹽霜,便成了大地的等高線。
兩根鋼軌的平行之美,在于它們永遠(yuǎn)守望卻不相交的克制。正是這種克制,讓南來(lái)北往的列車都能找到歸途。而枕木等距的空白,恰似人生必要的停頓——沒(méi)有這些沉默的間隔,再重的負(fù)荷也會(huì)壓垮前行的勇氣。
那個(gè)雨夜,我親眼看見(jiàn)一列貨車在小站人的保駕護(hù)航下,避開(kāi)了山體滑坡。每個(gè)選擇都是新的無(wú)私奉獻(xiàn)劇情,而我們的使命,就是確保安全暢通都不辜負(fù)責(zé)任。
當(dāng)汽笛聲刺破晨霧,整條山區(qū)鐵道線便蘇醒為大地譜寫(xiě)的五線譜。我們這些身著橘紅工裝的人,既是演奏者也是音符。你看那鋼軌盡頭閃爍的光點(diǎn),不是終點(diǎn),而是下一個(gè)彎道的開(kāi)始。
免責(zé)聲明:本網(wǎng)站所刊載信息,不代表本站觀點(diǎn)。所轉(zhuǎn)載內(nèi)容之原創(chuàng)性、真實(shí)性、完整性、及時(shí)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,請(qǐng)讀者僅作參考并自行核實(shí)。